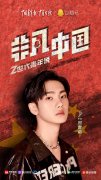子思:过去20年美西方对“中国大战略”的认知经历三次升级——特朗普20与美国大战
:特朗普有自己的大战略吗?或者,特朗普的大战略与一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有相关性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大战略这一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加上特朗普本人行为方式的随意性,使得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困难重重。
但是,未来数年内美国国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两者所决定的,为了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预测,也不得不认线与美国大战略的关系这个问题。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国内将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对手加以遏制、实施制裁甚至转入全面对抗的一派,其声音始终存在,这是因为这些声音一直以来都有其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的构成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共理论,二是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华理论,三是基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反中理论等。

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些理论在各种流行理论的相互竞争中时而因适用而强势、时而因不适用而弱势,导致基于这些理论的“遏制派”声音也时强时弱,从未消失。但毕竟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属于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由此而产生的反共、反华、反中理论在整个中美关系史上也就从未完全退场过。
一方面是在美国的单极霸权确立之后,美国大战略思潮再次兴起,各种意识形态都在大战略思潮中围绕着捍卫美国首要地位这个中心重新确立了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崛起,在构成重大挑战的同时,也在美国眼中成了和美国一样的具有大战略思维且在大战略执行能力上更胜一筹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反共、反华和反中理论都显得相对单薄了,从此不再作为单一因素起作用,它们被整合在了一个新型的美国大战略思潮当中。这个大战略思潮不仅包括了美国自身的“美国首要论”(Primacism)思潮,而且包括了将中国作为同样具有大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首恶论”思潮。
这个新的形势大大区别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最主要的特点是,美国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虽然表面上还体现为“接触派”和“遏制派”两大派,但争论的焦点和各自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一直以来以短期的、地区性的、经济导向的、局部范围的问题为主,逐渐转换到了目前以长期的、全球性的、战略导向的、整体范围的问题为主;从过去一直以来的一个常规战略格局,转化到了目前的一个大战略格局。
事实上,正是这个重大转换本身,大大增强了“遏制派”的地位。因为当短期利益、地区利益、经济利益、局部利益相对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接触派”一直以来所看重的利益交易也就不再重要,中美关系中的所谓“压舱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遏制派”一直以来所描绘的大风大浪也就预言成真了。
所以,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方在与美方打交道时明显感觉到的变化,如亲华派大批消失、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反华立场上高度趋同、美国媒体和政客在中国问题上呈现出“集体性思维”(Group-think)甚至“中国恐惧症”等,追根溯源,都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战略思维范式转移”导致的结果。
通过梳理自2005年至2024年近20年来,美西方战略学者针对他们眼中的“中国大战略”的分析和描述,大致可以看出,美西方这一围绕中国问题的“战略思维范式转移”,体现为三个阶段的“升级”。
第一级的时间段大约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期间首次出现了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视角和“以己度人”的心理,将当时快速崛起的中国判定为具有与美国大战略相匹敌并形成针锋相对之势的“中国大战略”的认知。
但是这一认知在当时的美国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即使有学者提了出来,也没有很快成为思考中美关系的主要认知框架。大多数的政策研究仍然聚焦于中国对美国大战略构成障碍的各个方面和具体形式;而正是这些方面和形式,主导了美国当时仍然各占半壁江山的“接触派”和“遏制派”之间相互争论,并成为中美高层级谈判之间各个议题的主要内容。

作者首次公开提出中国具有一个稳定的“中国大战略”(China’s Grand Strategy),他在书中写道:
“近年来,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备受关注。世界,尤其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新兴大国?明智的应对不仅需要弄清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程度,还需要回答一个未受足够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大战略是什么?”
从这个自设的问题出发,该书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以及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并探讨了具有大战略的中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新角色。
此后十多年里,戈德斯坦始终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相关文章还包括《中国现实而迫切的危险:现在是华盛顿担心的时候了》(《外交事务》2013年9/10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大战略》(《国际安全》2020年夏季号),《21 世纪的中美竞争:似曾相识和第二次冷战》(《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年6月)等。